“平原”是精神家园和写作领地
1 “我把人当‘植物’来写,要表现土壤与植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生命形态,我是有痛感的。”
记者:读你的长篇新作《河洛图》,以及前作《羊的门》《平原客》等,我都在想,相关题材要是换成功力稍逊的作家来写,很有可能会写成眼下习见的类型小说,因为这几部长篇写是的商场、官场、职场,以及家族、反腐等。当然,《城的灯》《生命册》等虽然写到相关行业或领域,相比要复杂一些。从文学角度看,类型小说多有较大的局限性。但你的写作却能跳出类型写作的窠臼,展现出大魂魄和大气象。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你一直在豫中平原这个背景下展开小说叙述,并且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,你总是能够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,对我们所面临的困境、我们的灵魂状况,进行非常有洞察力的追问。
李佩甫:我从来没有考虑,也没打算写类型小说。我的创作是这么来的,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,我就喜欢看书,也经历了各种事情,阴差阳错走进了文学的大门。刚开始写作的时候,我也没有什么方向,就是到处找素材,苦不堪言。直到1985年写出《红蚂蚱,绿蚂蚱》,我才算初步找到了写作方向。个人有个人的发展阶段吧,我只有写到那个阶段才发现自己还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,也就是豫中平原。而在以前,我都是写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。那么,找到这块矿藏以后,一开始我也只是写自己的童年、少年,也就是记忆中的一些东西,所以这块地方并不是很大的,但我慢慢写着,它就扩大成了整个平原。我说过,“平原”是生我养我的地方,是我的精神家园,也是我的写作领地。在一些时间里,我一直着力于写“人与土地”的对话,或者说是写“土壤与植物”的关系。我把人当“植物”来写,我就是要表现土壤与植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生命形态,这样写的时候,我是有痛感的。当然,我最早几乎都写的原生态,然后往前走,慢慢向内转,才开始切入平原的精神生态,这中间是有过程的。
记者:与写作相伴随,你对中原的认知,也定然是步步深入。
李佩甫:中原是一块绵羊地啊,它受儒家文化影响太深了。说老实话,汉字最早是刻在甲骨上、瓦片上,后来就刻到人心里去了。所以我说,我们的汉字是用鲜血喂出来的。这不是夸张的,是我见过很多世面后逐渐认识到的。走上写作道路后,我的生活面扩大了,走的地方也多,见识过三教九流的人物,和工农商学兵各个阶层都有过交道。无论是乡村,还是城市,我都有了解。年岁渐长以后,我越来越觉得,中原是被儒家文化驯服最深的一块地方。历朝历代,中原都遭遇过各种劫难。经历过漫长的时间以后,世世代代的老百姓就养成了一种骨头被打断,但又能粘起来的生命状态。它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百折不挠、生生不息。
记者: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性,也许在中原表现得突出一些。
李佩甫:我就觉得,儒家文化虽然有很多糟粕,但它最大的优点是它有很大的同化力和包容性。都说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顽强的民族,犹太人是最不容易被同化的。但在宋代时,犹太人中有一支逃难到当时的国都开封,在开封住下后就被彻底汉化了。历经这么长时间,现在看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我后来作为作家代表团成员去过以色列,参观他们的大流散博物馆,看到过相关的历史记录。现在开封有一些犹太后裔,也就几分之一犹太血统了,虽然他们中有愿意回以色列的,但他们的生活方式早已经完全被汉化了。
记者:这些看似和你的写作没有直接关系,但我想,正是这些思考构成了你写作的底蕴。所以读你的小说,能读到一种透彻的历史纵深感。
李佩甫:我说过一句话,中原是最代表中国的一块土地。我的想法是,这个被儒家文化浸润过的,被血肉喂养出来的民族,即使有一万个缺点,有一个优点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比不了的,就是繁衍力和生命力。我多年来一直想这个问题,想弄清楚汉民族、汉文化的发展轨迹,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一步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个人认为,这是我写作的研究方向,也是我长年寻找汉文化精神思维方向得出的判断。
记者:从开始写作,到最后找到方向,你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?
李佩甫:我1971年下乡,1974年上技校,学车工。1976年开始当工人,197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,1979年调到许昌市当文化局创作员,到了1985年写出《红蚂蚱,绿蚂蚱》,也就是说用了七年时间才找到写作方向。之前我当过工人么,写过不少工厂小说。那个时候就是编故事,找素材,写得很苦。等找到源泉后,写作就不那么苦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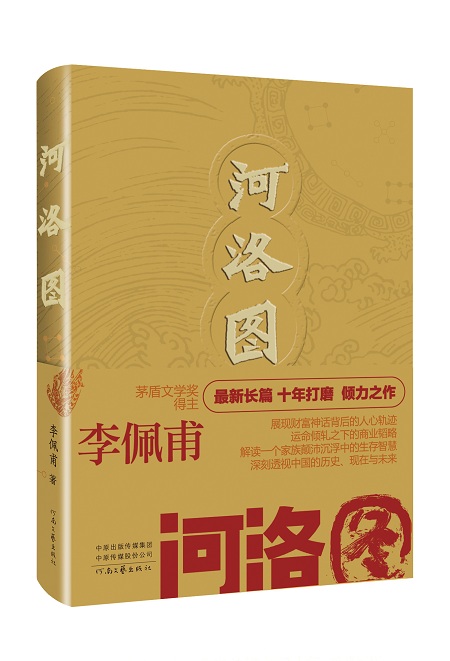
长篇新作《河洛图》近期推出
记者:在你的小说里,《河洛图》和《等等灵魂》似乎偏通俗一些。两部小说虽然写的不同历史年代,但都可以说是写商战的。《河洛图》里的康家像是靠着一份传说中的秘籍连福了十二代,《等等灵魂》里的转业军人任秋风却是在造就超市航母后,在各种利诱下迷失了灵魂,并且在权力欲驱使下盲目拓展,苦心经营的“商业帝国”崩塌。两者不同结局似乎隐含了什么。
李佩甫:是的,这两部作品都与写电视剧有关,当时是有时间限制的。写《等等灵魂》的时候,我仅仅写到了在高速发展的社会里,在到处都提倡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的时期,金钱和权力对人的压迫和冶炼。有些问题我一时还没想清楚。等到写《河洛图》的时候,这中间就有了一些思考的时间。所以,写这部长篇我给自己定下了两个主题:一,写一个特定地域的生存法则。二:时间。就是说,在大时间的概念里,任何智慧和聪明都是不起作用的。
记者:你在小说尾声里就写到“时间是有眼的”“在大时间的概念里,还有什么可说的呢?”,这些话里大概就反映了你说的第二个主题。小说引子,你写到风水师陈麦子一双眼睛能穿透三百年,应该有时间观上的考虑吧。因为单只是从故事情节看,不是非得有这个引子的。
李佩甫:我是觉得,一个三百年前的故事,是需要“天眼”的。所以,我借用了一个“大师”的眼睛。更重要的是,我想说,只有穿过历史才会发现,一个家族,无论多么富有,哪怕他是“神”,在大时代的变迁里,仍是很渺小的。
记者:的确如此。但把视线拉回到那个年代里,像康家少奶奶周亭兰就可以说用自己的身体力行,画了一个大写的“人”字。并且,她还为这个家族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。对比而言,同样是写商战,《等等灵魂》比较多写的尔虞我诈,《河洛图》却浓墨重彩写通识教育,也着实意味深长。
李佩甫:中原能够称之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,是有原因的。所谓的“文明”,以我个人的理解,就是用文字的形式把前人的经验、智慧、血泪凝结的教训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,传给后人,这才叫“明”。所以,一代一代的后人,以读书为做个“明白人”为始。这就是《河洛图》要阐释的意义所在。当然,文字也是可以“吃”人的,字背是有字的。就看你怎么去读了。
记者:像康秀才“留余”的理念,还是周亭兰“留余”的做法,从表面上看和《羊的门》里呼天成的“种人术”似乎有相通之处,用我们俗话讲,无论做官还是经商,首先都要把人做“好”。
李佩甫:“留余”中有一个很高尚的理念:“以不尽之巧以还造化”。什么是“造化”呢?那就是:大地、天空、阳光、流水,是大自然。这里提到的对大自然的“留余”,是极为超前的。尤其现在来看,它是在告诫后人,不要竭泽而渔。要给大自然留下修养生息的时间。
记者:这种理念很超前,可以看成是对儒家文化的继承性发展吧。
李佩甫:在中国当代大历史的框架里,包括儒家文化的底部,一直把“烈士”和“死士”放在了很值得尊崇的地位。这样的人太少了,也可以说是一代代活跃的“血分子”,是可以推动历史进程的“血分子”。尽管,历史基本上是统治者写就的,但古人是宁死也要留名的,今人与古人的差别是不同的“活法儿”。
记者:你的小说总体上对女性着墨不多,但《生命册》里的虫嫂让我读后深有触动。而且我觉得通过写虫嫂的遭遇,尤其是写她不被进城后的子女善待,你对城市病相剖析的力度,似乎不弱于一整本《城市白皮书》。怎么想到塑造这么一个人物形象?
李佩甫:写虫嫂这个人物,我是下了功夫的。虫嫂可以说是中原乡村的底版和基础。我觉得她与城市人的病相还是有很大差别的。她既是活的“细菌”,又是生生不息的源息。因为,她是有根基的。她与大地紧密相连。她几乎是不死的。她就是那个“春风吹又生”的草族。
2 “语言与思维方向是密切相关的,语言的表达方式也就是作家的思维方式。”
记者:如果说《河洛图》向“仁义礼智信”等中国文化传统优秀部分致敬,“平原三部曲”似乎涉及中西文化融合问题,尤其是《生命册》多少追问了终极价值问题。虽然你的写作给人感觉是纯中国的,但也不排除在思想上受西方文学影响吧。
李佩甫:有。读书,特别是读翻译的外国书对我影响巨大。青少年时期,我在许昌这个小城市读自己能找到的一切书。我父辈以上都不识字的,从小家里能看到的有文字的东西,就是半本黄历。但我就是喜欢看书,从童年到少年,我都是乱看书,什么书都看。只要是能找到的、能看得下去的书,我都看。看了不少书,但也是不求甚解。最早有好多字,我都认不得,所以很多年后,我明白那些字的意思,还是会把音读错。但早年读的那些书,对我有无声无息、或者说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记者:但你的写作从文字表达上,看不出多少西化的痕迹。我倒是在你的好几部小说、尤其是在“平原三部曲”里,看你写到一本叫《修辞学发凡》的书。
李佩甫:这是陈望道先生写的一本书,忘记是从哪儿得到的了。我小时候常读,都翻烂了。我把它带在身边,没书读的时候就翻开来看。也不是认真读,但这样翻翻,对我是有影响的,尤其对我在语言的修饰上有很大影响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,这本书里讲到对推敲的认识。有个地方举例说,杜甫写过著名的《秋兴八首》,其中有一联:“香稻啄馀鹦鹉粒,碧梧栖老凤凰枝”。陈望道说,杜甫这诗写得过分雕琢。陈望道要求表达的准确,反对雕琢。他对语言文字的这种认知和解读,对我是有影响的。
记者:你有一句话,语言就是思维。我读后印象深刻。
李佩甫:我是觉得,文学语言跟认知有很大关系。你的认识不到那一步,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表达。语言与思维方向是密切相关的,语言的表达方式也就是作家的思维方式。可以说,每一种表达,都渗透着作家的生命体验和思维过程,都囊括了不同作家不同的生存地域、不同的血脉迁徙、不同的水土气候,等等。在我看来,表达的差别就是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差别。所以说,语言就是思维。
记者:但我们通常只是说,语言是思维的一种体现。
李佩甫:文学语言就是作家思维的体现。文字不只是文字本身,文字作为人类精神的物质外壳,是人类智慧的结晶。它是先导,是标尺,是人类透视力和想象力的极限。从我自己来说,我每次为了找到准确的表达方式,尤其是为了写好开头,会费很多心思。为啥呢?因为开头第一句,会决定整部作品的情绪走向。所以说,写好开头,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。为写好第一句,有时需要等一个月,有时需要等上一年半载。比如写《生命册》,我写了八个开头,最长的写到八万字,都废掉,就因为没有找到第一句话。那段时间,实在写不下去了,我就跑到乡下去住了几个月,吃了几箱子方便面。我是去找感觉的,我要把我所理解的声、光、色、味找回来。从乡下回来后,我还从书房里搬出来,换了个房间再坐下来,于是有了那句“我是一粒种子”,这样才算找到了准确的语言情绪,才终于写了下去。
记者:你的写作是否受过《红与黑》的影响?你小说里的很多人物,像《羊的门》里的呼国庆、《城的灯》里的冯家昌、《平原客》里的刘金鼎等等,在某种意义上都称得上是“野心家”。而且你对这类人物心理的把握和刻画,像是得了司汤达的“真传”。
李佩甫:《红与黑》很早的时候读过,但都忘了。我的那些人物是有野心的,但我没想写野心家。我想写的是啥?写我们民族中的一些活跃的“血分子”,写他们行走的轨迹。我觉得,我实际上是写这块土地上长得最好的植物是啥样。海德格尔说,建筑一旦矗立在大地上,它就是有生命的。植物也是这样的,我就是想写出这株“植物”能长成什么样,写出他行进的过程,写他的生长状态和生长危机。
记者:但我觉得,你真是擅长写这类人物,其中有些笔触,用所谓“入木三分”来形容也不为过。
李佩甫:我过去看大仲马的《基督山伯爵》,老雨果的《九三年》。对其中的一些人物印象深刻。像《九三年》开头部分,写一艘战船在恶劣天气行驶在大海上,一门大炮挣断固定的螺栓横冲直撞,一艘船快要完蛋了,这时候一个人挺身而出,终止了悲剧的发生。用老雨果的话讲就是,蚂蚁战胜了庞然大物。在关键时刻,这样的优秀分子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。我们中华民族有许多这样的优秀分子,从春秋时代看起,不也是人才辈出?当然,要说怎么算是优秀,东西方是有差别的。
记者:无论你写城市与乡村,都包含在书写平原的这个大背景里。有意思的是,你虽然是城里人,但大概从写《李氏家族》开始,你写作重心都在写农村,或者说你笔下的人物,大多都有农村生活背景。
李佩甫:是啊,按说我在城市生活时间最长,我在郑州都生活了36年了。对于乡村也就童年、青年时期的一点记忆,但我确实写乡村更有感觉。这是“根”的问题,童年伴随人一生啊。我生在工人家庭,算是城里孩子,但少年时期有很多时间是在乡下姥姥家度过的。在那时,我就认识了平原上各式各样的草,这种草的形状和气味一直伴随我,浸润在我的血液里。我在很长时间里,在人生行走的旅途中,都觉得自己是平原上的一株草。再后来,我又在1971年下乡当了知青,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农忙的时候,我干各种各样的农活,农闲的时候,我作为生产队长,还常常与那些支书、队长到公社开会。所以,我觉得平原实际上就是我的家乡,也是我的写作领地。
3 “我写平原这片土壤,围绕的都是对汉文化思维方向的观察和追寻这个中心。”
记者:应该说,你塑造了不少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,你着重强调的平原反倒会因此被忽略。同样,你小说的叙述有着坚实的质地,与叙述看似游离的部分就可能不是那么被关注。但就我的阅读观感,这部分带有词条性质的内容,无疑让你小说的大厦更为结实,更何况这些“词条”也写得特别出彩。像《羊的门》里的易筋经和十法则,以及《城的灯》里的“上梁方言”注释和刘汉香种花“观察日记”。应该说,这部分内容对你写豫中平原这个背景也起到了深化的作用。这些词条你是借鉴了相关资料,还是主要出于你个人的解读?
李佩甫:都是我个人的解读。但易筋经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的,我知道也有人在练,我有个朋友,原来身体是很不好的,他每天练功三次,如果不练这个功,他身体早就垮了。中华传统文化里头是有很多奇特的东西的,很厉害,厉害得不可想象。易筋经在我国一些典籍里头也有记载,练功的状态我也知道,也是有参照的,这些东西我都用在这个小说里头了。
记者:那其他呢,像十法则,还有上梁方言等,都是你虚构出来的?
李佩甫:我虚构的,是我个人的创造,但融入了我个人对这块土地的理解。我是贴近这块土地,去理解它的。这都没有虚的,全是真切的。还真是,咱俩今天聊,有两点我是特别高兴的。《生命册》最后一章,我认为是写得最好的,但从来没人跟我说起过,你今天说到了。还有你说到《城的灯》里“上梁方言”注释写得很好,也是从来没人这么说过,你说到了,也说对了,我认为这是我在这些小说里写得最好的部分。
记者:这些部分的确容易被忽略。很少有作家像你这么用心去创造词条,而且在多数小说里,这样的词条只能算是旁逸斜出,只是对故事情节发展起辅助性的作用,它们在你的小说里却无疑是重要的,就像方言也在你的小说里起到强化和深化背景的作用一样。
李佩甫:对,我的小说里会融入方言,但不是按原生态的样子放进去,而是经过了思维认知的转化。也就是说,进入我小说里的方言,都是修正过的。我写平原这片土壤,也有一个调试和修正的过程,围绕的都是对汉文化思维方向的观察和追寻这个中心。我想搞明白我们汉民族是怎么走过来,为什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,有可能成为什么样子。
记者:就像你说的,语言就是思维,那我觉得方言更是思维。
李佩甫:相比普通话,方言更具象,它代表的是人们在某个阶段,对某种事物或现象的认知。它的出现和发展是有过程的。像“互联网”这样的新词,也只有到了现在才可能出现,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出现的。
记者:也就是说,通过学习方言,写作方言,加深了你对平原这片特定地域在某一个或几个特定阶段的认知。
李佩甫:对,通过方言更能理解这块地方的生存状态。
记者:你的小说很少线性写一个人的发展轨迹,倒是比较多由一个人串联起一群人,或是先写一个人,再慢慢切入写整个地域。所以,你的小说偏于树型结构或网状结构,要做到形散而神不散是有难度的。
李佩甫:因为我主要写关系,写土壤和背景。马克思有句话说,人是生产关系的总和。人不只是人本身啊,他背后有一个巨大的,一般人看不到的背景。有时候,我们评价一个人很难准确,就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后面站着什么,他是怎么走过来的。这个背景对人的影响真是特别大。我是主要写背景的,不是写单个的人,我们单个的人都是在这个巨大的背景中生活。我们有时觉得一个人的举动很荒诞、很突然,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后面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。我是想把背景写出来,我个人认为,这背景的力量是巨大的,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还要大。
记者:那你会不会担心,用过多笔墨写背景,会不会反而把人物给冲淡了。
李佩甫:我把所有的人物,都放到我最熟悉的环境里写。不然我怎么写?像美国纽约,我只是去过而已,只有那么一点浮光掠影的印象,我不可能深入骨髓去写。只有把人物放到我熟悉的情境里,我写起来才得心应手。
记者:从你的作品里,还是能读到上帝视角。这可能是因为你在小说里融入了一点近似神性的东西。
李佩甫:一个民族是需要一点神性的。
记者:都说现实充满魔幻色彩,你着重书写的权力就更有魔幻性了,但你的小说却似乎和魔幻现实主义沾不上边。
李佩甫: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很大啊,我刚读到《百年孤独》的时候是相当震惊的。拉美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也有相似性,在近现代都处于被奴役状态。他书里有些带魔幻色彩的细节,像拉磁铁,跟我们童年时候玩的推铁环就很相似。当然他的描写,什么钉子、铁锅跟着满街跑是夸张的。但拉美作家在有些思想意识上是超出中国作家的,他们能穿越历史,穿越具象。
4 “文学不是用来经营的,进入文学深处,你就无处可藏了。”
记者:还是回来说说平原。你小说里固然写到一些充满进取精神的活跃分子,但尤其不能忽略的是那些承受者的形象,这其中以女性为主。
李佩甫:我写的都是平原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,平原上的老百姓只有忍和韧,也没什么革命性。我和陈忠实写的也不一样,因为历史状况不同,写的地域也不同,他写的八百里秦川,站在黄土高原上是可以大声喊出来的,但在河南这块土地上,很多东西都是得咽下去的,所以我是写隐忍的。这样的隐忍靠一口气来支撑,很苦啊。但用“忍”和“韧”这两个字来概括中原文化是最准确的。我有时候觉得,河南老百姓就像土地一样沉默,那是一种集体无意识,他们就靠一口气,一代代存活了下来。
记者:你受益于大量阅读,但读你的小说,看不太到西方文学的影响。你像是一直都坚定地走中国化、本土化的写作路子。
李佩甫:我的写作没和西方对接,算是比较中国化吧,比有些作家更本土,更传统一点。但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和其他作家一样,都拼命吸收西方各种文学流派营养,也都不同程度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。那时,我可以说也吃了一肚子“洋面包”,感觉很胀,消化不了啊。所以在写作上特别迷茫,有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像狼一样在街头徘徊。那时,我已经知道文学不仅仅是写好一个故事了,搞好写作需要找到一种独一无二的表达和认知方式。但“洋面包”好吃,我却长了一个食草动物的胃,所以特别痛苦。
记者:尝试过西方化的写作吗?
李佩甫:我学着写过意识流作品,但怎么写都觉得不成功,也没好意思发出去。这跟我当时还没找到认知的方向有很大关系。我觉得,认知或者说创造性地透视一个特定的地域是需要时间的,不光需要时间,还需要认识。我说过一句话,时间是磨,认识是光。磨和光都有了之后,我才找到写作方向,也才有了《红蚂蚱,绿蚂蚱》。当然这也不是说我完全回归传统,才找到方向。实际上,一些现代派作品,像普鲁斯特、乔伊斯,还有克洛德·西蒙等作家的写作,我还是接受的,也是对我写作有影响的。
记者:体现在哪些方面?
李佩甫:他们小说语言里那种声光色味,描写细节的准确程度等等,对我有影响。当然我写出来的味道,还是平原的味道。所以,我不像一些作家那样去仿制。你那样仿制,在刚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会沾一点光,新锐编辑喜欢,但长期那样写就不行了。我是觉得我们不能跟着西方亦步亦趋,也没这个必要。我们得写自己的生活,得把根扎在自己的土壤上。你在自己的土壤上,对这个地方熟悉,你就可以感觉到它的味道,你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,感知到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。也只有这些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,是别人夺不走的,所以我觉得不能一味学西方。只有找到你自己的领地,写你最熟悉的东西,才能做到左右逢源,得心应手。反之,你会捉襟见肘,很难远行。
记者:你的写作总体看挺真诚的,比较少私心杂念,也比较少条条框框。
李佩甫:你说我真诚,那是我把自己放进去,在写作中把我对土地的理解都放进去了。我觉得,作家情感的真诚度对作品质量有很大影响。文学不是用来经营的,虽然现在文学场有了些变化,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仍然是相对纯粹的。文字骗不了人,刚开始写的时候看不大出来,靠编造也能蒙混过关,但等到进入文学深处,你就无处可藏了。你的心性,你的小伎俩,都很容易被内行人一眼看出来。所以写作不能有偷工减料的心理,文字这东西一旦滑下去就很难再上来了,你得咬住、坚持住。
记者:读你们这一代作家的处女作,再对比后来的写作,回看你们蜕变成蝶的过程会很有意思。你熟读西方经典著作,写的却是中国化的小说,倒是觉得你适合来谈谈什么是“伟大的中国小说”这个话题。
李佩甫:我不知道什么是“伟大的中国小说”,但我知道中国作家都想写出本民族所期待的,好的文学作品。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从文本角度,如何突破旧有的文学样式?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一个困境。从内容角度,文学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,应该是“麦田的守望者”,但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,我们思考的时间还远远不够。在这个时期,我们的文学落后于时代。如果文学落后于时代,作家仅仅是描摹现实生活贩卖低劣商品的“故事员”,那么我们的写作是有问题的。
记者:但另一方面,网络化时代全民写作。至少从表面上看,我们的写作似乎是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多元。
李佩甫:多元化是好事,全民写作也是好事。但文学创作不只是写一个故事,或者说写一种经历。文学创作也不是生活本身,作家只有用认识的眼光照亮生活、用悲悯的眼光认识生活,用独一无二的方式表达生活,在作品中加入意义的创造,融入自己的思想,才能成就真正的文学作品。文学一旦失去了应有的水准和品格,失去了应有的境界和探索精神,失去了文学语言应有的思辨性和想象力,结果必然是庸俗化的泛滥。一个民族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的先导,是很悲哀、也是很痛苦的。所以我觉得,现在还不是谈“伟大的中国小说”的时候。
上一篇:杨绛:每个人都有双重本性
下一篇:作家要有正常人温度和态度的话
推荐文章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