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华谈写作,成功的人原来是这么来的
杨绍斌:你通常是怎么构思一篇小说的?
余 华:我写作的开始五花八门,有主题先行,也有的时候是某一个细节、一段对话或者某一个意象打动了我,促使我坐到了写字桌前。
杨绍斌:《活着》这部小说里福贵这个形象有来源吗?
余 华:福贵最早来到我脑子里时是这样的,一个老人,在中午的阳光下犁田,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,皱纹里嵌满了泥土。
杨绍斌:许三观呢?
余 华:他最早的形象是在冬天的时候穿着一件棉袄,纽扣都掉光了,腰上系着一根草绳,一个口袋里塞了一只碗,另一个口袋里放了一包盐。但是,这是我开始写作时的形象,构思的时候还不是这样。
杨绍斌:那又是怎么样的?
余 华:关于《活着》,我最早是想写一个人和他生命的关系,这样的关系在很长时间里都让我着迷,这有点主题先行,可是我一直不知道这篇小说应该怎么写。有一天早上醒来时,我对陈虹说,我知道怎样写这篇小说了,因为我想出了题目,叫《活着》。陈虹说这个题目非常好。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标题,才有了这部小说。有时候一个标题也会让你写出一部小说。八十年代的时候,文学界批判过主题先行的写作方式,其实完全没有道理,写作什么方式都可以,条条大路都通罗马。
至于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最早是这样的,大概是在1990年,我和陈虹在王府井的大街上,突然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泪流满面地从对面走了过来。我们当时惊呆了,王府井是什么地方?那么一个热闹的场所,突然有一个人旁若无人、泪浪满面地走来。这情景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到了1995年,有一天中午,陈虹又想起了这件事,我们就聊了起来,猜测是什么使他如此悲哀?而且是旁若无人的悲哀!这和你一个人躲到卫生间去哭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杨绍斌:所以后来在小说里,许三观在大街上哭。
余 华:这已经是最后一章了。那天,我们两个人不断猜测使那位老人悲哀的原因,也没有结果。又过了几天,我对陈虹说起我小时候,我们家不远处的医院供血室,有血头,有卖血的人。我说起这些事时,陈虹突然提醒我,王府井哭泣的那位老人会不会是卖血卖不出去了,他一辈子卖血为生,如果不能卖了,那可怎么办?我想,对,这小说有了。于是我就坐下来写,就这么写了八个月。
杨绍斌:许三观后来就卖不了血。
余 华:当时我认为小说最后的高潮,就是他卖不了血,所以他就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哭,因为这意味着他失去了养活自己的能力,他的悲哀是绝望以后的悲哀。这对年轻人来说没什么,可是对一个老人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曾经准备在这最后的一章里重重地去写,准备将自己吃奶的力气都写光,将这一章充分渲染。可是当我写完第二十八章,也就是结尾前的一章后,我才知道叙述高潮其实是在这一章,就是许三观一路卖血去上海的那一章,于是最后一章我很轻松地完成了。根据我写作和阅读的经验,两个很重的章节并排在一起,只会互相抵消叙述的力量。

杨绍斌:这么说来,你在动手写作时,对笔下的人物已经胸中有数了?
余 华:还是没数,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他会干什么,最多只能先给他一些设计,而且有些还用不上。
杨绍斌:你现在还拟提纲吗?
余 华:我在旧信封上做笔记。开始时我怕自己忘了,就随手拿起一个旧信封记上,一个记满了,再用第二个,为了风格的统一,我接下去仍然用旧的信封。像《活着》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我都写满了一堆旧信封。现在我开始用新的信封,而且必须是国际航空的那一种,上面没有邮政编码的红框,显得更干净。这已经成为了我的写作习惯。当我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,我只要知道开头一万多字怎么写就行了,后面肯定会出来。要是一万字写完了,后面还不出来,那就不应该写了。这和我早期的写作已经很不一样了。我以前小说里的人物,都是我叙述中的符号,那时候我认为人物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,他们只要传达叙述者的声音就行了,叙述者就像是全知的上帝。但是到了《在细雨中呼喊》,我开始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,我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声音,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。因此,我写《活着》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的过程,其实就是对人物不断理解的过程,当我感到理解的差不多了,我的小说也该结束了。我想起来,1987年在黄山的时候,有一天傍晚我和林斤澜一起散步,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和汪曾祺一起去看望沈从文先生,他问沈先生小说应该怎么写,沈先生只回答了一个字:贴。就是说贴着人物写。这个字说得多好!可是当时我没有很深的感受,现在我才发现的确如此,贴——其实就是源源不断地去理解自己笔下的人物,就像去理解一位越来越亲密的朋友那样,因此生活远比我们想像的要丰富的多,就是我自己也要比我所认为的要丰富的多。
杨绍斌:你对小说的开头一句敏感吗?
余 华:非常敏感。第一句要是写不好,下面的话就白写了。小说的第一句话,就好比一个人刚从子宫里出来,要是脑袋挤扁了,这个人就不会聪明。
杨绍斌:你喜欢在白天还是晚上写作?
余 华:不分白天晚上,我只要吃饱了和睡足了,任何时候都能写作。
杨绍斌:你写得慢吗?
余 华:我现在比以前快多了。我现在真正写作的时间不多,一旦写起来,就很快。我觉得写作也是一门手艺,熟练之后工作就会变得轻松起来;可是另一方面,压力也加重了,我现在已经写了一百多万字了,这对我来说是个包袱,我应该如何去面对我过去的作品?有时候这是很困难的。
杨绍斌:有些作家总是越写越困难。
余 华:所有的作家都应该是越写越困难,当我拥有二百多万字的作品时,我想我会更困难。我庆幸人不能活得更长久,要不这作家没法当了。如果我能够活五百年,那么六十岁以后我肯定不当作家了。
杨绍斌:你在写作中会碰到哪些具体的困难?
余 华:可以说非常多。有很多都是细部的问题,这是小说家必须去考虑的,虽然诗人可以对此不屑一顾,然而小说家却无法回避。所以我经常说,小说家就像是一个村长,什么事都要去管。
杨绍斌:他得充分顾及到细节的清晰和真实。
余 华:是的,比如说福贵这个人物,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,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,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,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写,必须时刻将叙述限制起来,所有的语词和句式都为他而生,因此我连成语都很少使用,只有那些连孩子们都愿意使用的成语,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。
杨绍斌:它对你的限制很大。
余 华:是的,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写作就放弃了叙述上的追求,相反,这时候的叙述更需要作家下功夫。比如小说中有这么一段,就是有庆死后,福贵瞒着家珍将有庆埋在一棵树下,然后他哭着站起来,他看到那条通向城里的小路,有庆生前每天都在这条小路上奔跑着去学校,这时福贵再次去看这条月光下的小路。我感到必须写福贵对小路的感受,如果不写,作为一个作家是不负责任的,可是如何去写?我记得自己曾经在《世事如烟》里有过这样的描述,说月光下的道路像河流一样,闪烁着苍白的光芒。如果这时候用这样的句子来描述一个失去了儿子的父亲,显然是太不负责任了。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意象,我费了很长时间,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意象——盐,我这样写道:那条通向城里的小路像是撒满了盐一样。对于一个农民来说,盐是非常重要的;另一方面,又符合他当时的心情,就像往他伤口上撒了盐一样。
杨绍斌:是的,我读到这一段时很感动。
余 华:有时候写作中碰到的困难,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,可是会阴差阳错地要了作家的命,甚至会让作家感到自卑,感到自己再也写不下去了,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,可是后来他会突然发现那其实是一个很小的问题,随手一写就解决了。就像是抱着孩子到处找孩子,戴着眼镜到处找眼镜,就是这样的困难,会让作家写作的过程越拉越长。
杨绍斌:具体说呢?
余 华: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具体的例子,但它确实是我写作时随时都要遇到的困难。可以这么说,什么是叙述?它在确立前其实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困难,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和它们相遇的过程,不断地去克服它们的过程,最后你才会发现一个完整的叙述成立了。我在写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时,碰到这样一个难题,那就是如何让许玉兰给许三观生下三个儿子。在其他方式的叙述里,这一章可以不写;可是在这部作品中,我觉得必须写。虽然这部作品是跳跃的,而且十分简洁,可是它在叙述上对人物每一段经历都是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后来,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,让许玉兰骂起来。这是第四章,整个一章,都是许玉兰躺在医院的产台上骂许三观。生第一个儿子时,许玉兰骂得仇恨无比;第二个骂到一半时,孩子出生了;第三个才骂了两声,孩子就出来了。不是有个说法吗,女人在生孩子时是很恨男人的。许玉兰在产台上骂了三次,叙述里的时间一下子过去了很多年。其实这样的方式我在《我没有自己的名字》里就已经使用过了,我让来发将父亲三十多年间对他说的话在一个句子里完成。一个一百多字的句子一下子将三十年的时间打发走了,这是我写作最得意的时候。人的记忆就是这样,我父亲在三十年间对我说的不同的话,我可以在一分钟里集中起来。
杨绍斌:你修改吗?
余 华:我是一个热爱修改的作家,我觉得修改是一种享受,而且修改的过程是我对自己一个内省的过程,这对我以后的写作都会有帮助。
杨绍斌:你是否跟别人谈论你正在写的小说?
余 华:以前我经常谈,现在不谈了。以前我的写作方式决定了我可以和别人谈,因为在写之前我已经知道得很多;现在我写之前知道的不多了,所以我不谈了。
杨绍斌:你对自己的小说语言有些什么要求?
余 华:我对语言只有一个要求:准确。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像地主压迫自己的长工一样,使语言发挥出最大的能量。鲁迅就是这样的作家,他的语言像核能一样,体积很小,可是能量无穷。作家的语言千万不要成为一堆煤,即便堆得像山一样,能量仍然有限。
杨绍斌:你离开海盐去北京也有十多年了,脱离家乡的语境和生活,这种迁移本身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变化,对你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?
余 华:影响是多方面的,不过决定我今后生活道路和写作方向的主要因素,在海盐的时候已经完成了,应该说是在我童年和少年时已经完成了。接下去我所做的不过是些重温而已,当然是不断重新发现意义上的重温。我现在对给予我成长的故乡有着越来越强烈的感受,不管我写什么故事,里面所有的人物和所有的场景都不由自主地属于故乡。
杨绍斌:你认为你的写作和家乡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联系?
余 华:我只要写作,就是回家。当我不写作的时候,我才想到自己是在北京生活。
杨绍斌:你喜欢哪些作家?
余 华:我喜欢的作家太多了。
杨绍斌:最早的时候你喜欢川端康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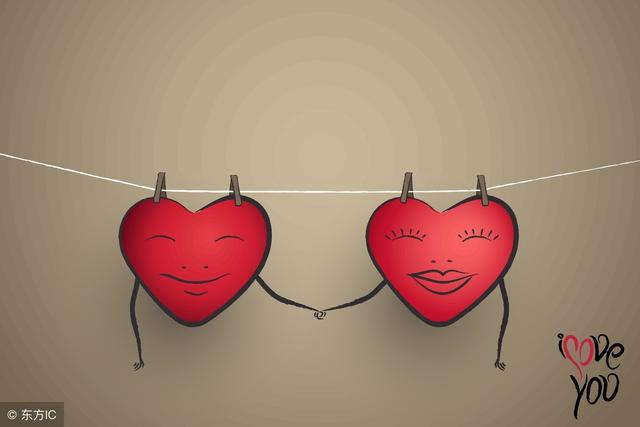
余 华:是的。1980年,我在宁波的时候,在一个十多个人住的屋子里,在一个靠近窗口的上铺,我第一次读到了他的作品,是《伊豆的歌女》,我吓了一跳。那时候中国文学正是伤痕文学的黄金时期,我发现写受伤的小说还有另外一种表达,我觉得比伤痕文学那种控诉更有力量。后来,有五六年的时间,我一直迷恋川端康成,那时候出版的所有他的书,我都有。但长期迷恋一位作家,对一个想写作的年轻人来说,肯定是有害的。接下来是卡夫卡,我最早在《世界文学》上读过他的《变形记》,印象深刻,过了两年,我买到了一本《卡夫卡小说选》,重新阅读他的作品,这一次时机成熟了,卡夫卡终于让我震撼了。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《乡村医生》里的那匹马,我心想卡夫卡写作真是自由自在,他想让那匹马存在,马就出现;他想让马消失,马就没有了。他根本不作任何铺垫。我突然发现写小说可以这么自由,于是我就和川端康成再见了,我心想我终于可以摆脱他了。
杨绍斌:大概就是在那个时期,你写出了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。
余 华:是的,我写出了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,当时我很兴奋,发现写出了一篇让自己都感到意外的小说,不过我还是没有把握,刚好我要去北京,去参加《北京文学》的笔会,就将小说拿给李陀看,李陀看完后非常喜欢,他告诉我,说我已经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。李陀的这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,就是他这句话,使我后来越写胆子越大。
杨绍斌:就是说卡夫卡成了你创造力的第一个发掘者。
余 华:可以这么说。不过我现在回头去看,川端康成对我的帮助仍然是至关重要的。在川端康成做我导师的五六年时间里,我学会了如何去表现细部,而且是用一种感受的方式去表现。感受,这非常重要,这样的方式会使细部异常丰厚。川端康成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作家。就像是练书法先练正楷一样,那个五六年的时间我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写作基础,就是对细部的关注。现在不管我小说的节奏有多快,我都不会忘了细部。所以,卡夫卡对我来说是思想的解放,而川端康成教会了我写作的基本方法.在喜欢川端康成的那几年里,我还喜欢普鲁斯特,还有英国的女作家曼斯菲尔德,等等,那时候我喜欢的作家都是细腻和温和的。卡夫卡之后,我开始喜欢叙述和情感都很强烈的作家。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发现我喜欢的作家越来越多了,而且已经没有风格上的局限了。
杨绍斌:你说说看,还有哪些作家?
余 华:比如说鲁迅。鲁迅是我至今为止阅读中最大的遗憾,我觉得,如果我更早几年读鲁迅的话,我的写作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状态。我读鲁迅读得太晚了,虽然我在小学和中学时就读过。
杨绍斌:因为原先几乎是一种被动接受。
余 华:其实鲁迅是不属于孩子们的。我非常惊讶地发现,我小时候都背通过的《孔乙己》、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等作品,当我前年重读时,就像是第一次阅读,读完了才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可见那时候我其实是没有阅读鲁迅,或者说只是旅游而已,现在我的阅读是在鲁迅的作品里定居了。重读鲁迅完全是一个偶然,大概两三年前,我的一位朋友想拍鲁迅作品的电视剧,他请我策划,我心想改编鲁迅还不容易,然后我才发现我的书架上竟然没有一本鲁迅的书,我就去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鲁迅小说集》,我首先读的就是《狂人日记》,我吓了一跳,读完《孔乙己》后我就给那位朋友打电话,我说你不能改编,鲁迅是伟大的作家,伟大的作家不应该被改编成电视剧。我认为我读鲁迅读得太晚了,因为那时候我的创作已经很难回头了,但是他仍然会对我今后的生活、阅读和写作产生影响,我觉得他时刻都会在情感上和思想上支持我。鲁迅可以说是我读到过的作家中叙述最简洁的一位,可是他的作品却是异常的丰厚,我觉得可能来自两方面,一方面鲁迅在叙述的时候从来不会放过那些关键之处,也就是说对细部的敏感。要知道,细部不是靠堆积来显示自己的,而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,又在一些关键的位置上恰如其分地出现,这时候你会感到某一个细部突然从整个叙述里明亮了起来,然后是照亮了全部的叙述。鲁迅就是这么奇妙,他所有精彩的细部都像是信手拈来,他就是在给《呐喊》写自序时,写到他的朋友金心异来看望他,在如此简洁的笔调里,鲁迅也没忘了写金心异进屋后脱下长衫。看上去是闲笔,其实是闲笔不闲。用闲笔不闲来说鲁迅的作品实在是太合适了。在《孔乙己》里面,当写到孔乙己最后一次来酒店时,他的腿已经断了。如果孔乙己腿没有断,可以不写他是如何来的,可是他的腿断了,就必须要写,这是一位优秀作家的责任感。鲁迅先是让他的声音从柜台下飘上来,然后让小伙计端着酒从柜台绕过去,看到孔乙己从破衣服里摸出了四文大钱,这时候叙述就看到了他满手的泥,鲁迅这样写: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。鲁迅的交待干净有力。鲁迅作品有力的另一个方面,我想应该是鲁迅的宽广,像他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,他在写百草园时的叙述是那么的明媚、欢乐和充满了童年的调皮,然后进入了三味书屋,环境变得阴森起来,孩子似乎被控制了,可是鲁迅仍然写出了童年的乐趣,只是这样的乐趣是在被压迫中不断渗透出来,就像石头下面的青草依然充满了生长的欲望一样。这就是鲁迅的宽广,他没有将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对立起来,因为鲁迅要写的不是百草园,也不是三味书屋,而是童年,真正的童年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。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.我想起来当年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发表时,美国很多批评家都认为老人象征什么,大海又象征什么。海明威非常生气,他认为老人就是老人,大海就是大海,只有鲨鱼有象征,他说鲨鱼象征批评家。然后他给自己信任的一位朋友贝瑞逊写信,希望他出来说几句话,贝瑞逊的回信是我读到的对象征最好的诠释。贝瑞逊说老人确实就是老人,大海也就是大海,它们不象征什么,但是,贝瑞逊最后说,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又是无处不洋溢着象征.一个真正的老人,一个真正的大海会拥有多少象征?只有这样的形象才是无处不洋溢着象征。鲁迅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,写出的就是真正的童年,无处不洋溢着象征的童年。我一直非常喜欢艾萨克·辛格的哥哥对他说的那句话: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的,只有事实不会陈旧过时。
杨绍斌:普鲁斯特对你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?
余 华:普鲁斯特总是能够绵延不绝地去感受,他这方面的天赋其实远远长于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长度。他的感受是那样的独特,同时又是那样的亲切,让人身临其境。他就是在自恋的时候也是非常可爱,当他写到晚上靠在枕头上睡觉时,就像是睡在自己童年的脸上,娇嫩清新。
杨绍斌: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在细雨中呼喊》,我觉得在风格上的细腻与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有某种联系。
余 华:我希望有。乔伊斯我也很喜欢,因为我找到了阅读《尤利西斯》的最好办法,那就是随手翻着去阅读,你会发现这个伟大的作家对细部的刻画可以说是无与伦比,当他写一个人从马车里出来时,会有一连串的动作,先是用手推一下,然后用胳膊肘去撞,最后是用脚将车门踢开了。
杨绍斌:另外还有哪些作家?
余 华:进入九十年代以后,我最迷恋的作家是但丁和蒙田。蒙田随笔中对人与事物的理解是那样的温和,同时又那样的充满了力量,那种深入人心的力量。所有的法语作家里,我最热爱蒙田;所有的意大利语作家里,我最热爱但丁;西班牙语应该是塞万提斯;德语可能是歌德;俄语当然是托尔斯泰;至于英语世界里,我还找不出一个我最热爱的作家,莎士比亚有这样的可能,如果他作品中的毛病少一些的话。我对他们的热爱毫无功利之心,不像刚开始写作时那样想学到点什么。刚开始写作时,卡夫卡、川端康成这样的作家很大程度就像是在我身上投资,然后我马上就能出产品,他们就像是一个跨国公司似的。而现在对但丁和蒙田,我是怀着赤诚之心去阅读。
余 华:布尔加科夫是这样的,读到以后大吃一惊。然后我才感到对苏联文学的了解是多么不容易,这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。最早我们知道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,或者是法捷耶夫……
杨绍斌:后来是《静静的顿河》。
余 华:肖洛霍夫,那是一位伟大的作家,这一点无可非议。然后突然发现还有索尔仁尼琴、帕斯捷尔纳克。我原以为苏联文学到这两位已经见底了,想不到还有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——布尔加科夫,他是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。
杨绍斌:像深渊一样。
余 华:真像是进入了深渊。布尔加科夫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,我非常喜欢他,尤其是他的《大师和玛格丽特》,读这部作品时,我发现有些辉煌章节的叙述都是布尔加科夫失控后完成的,或者说是他干脆放任自流。这给我带来了一点启示,那就是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,不要剥夺自己得来不易的自由。
杨绍斌:再谈谈加西亚·马尔克斯吧。
余 华:我是1983年开始读他的小说的,就是《百年孤独》。那时候我还没有具备去承受他打击的感受力,也许由于他的故事太庞大了,我的手伸过去却什么都没有抓到。显然,那时候我还没有达到可以被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作品震撼的那种程度。你要被他震撼,首先你必须具备一定的反应,我当时好像还不具备这样的反应。只有觉得这位作家奇妙无比,而且也确实喜欢他。其实拉美文学里第一个将我震撼的作家是胡安·鲁尔福。我记得最早读他的作品是他的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,那是在海盐,虹桥新村二十六号楼上三室,你不是来过吗?我当时读的是人民文学版,题目是《人鬼之间》,很薄的一本,写得像诗一样流畅,我完全被震撼了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,我当时已经写作了,还没有发表作品,正在饱尝退稿的悲哀,我读到了胡安·鲁尔福,我在那个伤心的夜晚失眠了。然后我又读了他的短篇小说集《平原上的火焰》,我至今记得他写到一群被打败的土匪跑到了一个山坡上,天色快要黑了。土匪的头子伸出手去清点那些残兵们,鲁尔福使用了这样的比喻,说他像是在清点口袋里的钱币。
杨绍斌:最后一个问题,假如可能的话,在你阅读过的文学作品中,你愿意成为哪一部作品的作者? .
余 华:我愿意成为《圣经》的作者。但是给我一万年的时间,我也写不出来。
下一篇:迟子建:人有故乡是幸运的
推荐文章:
